「追劇」不光是一種娛樂,更是參與朋友圈的重要話題,像是問:「你最近在追哪部?」、「OO劇你追了嗎?」要是不說幾部劇名,好像就難接上話題。
研究中國古典戲劇的汪詩珮教授告訴我們,「追劇」並非是現代人的專利,其實中國古人也愛追劇,只不過看的是中國古典戲劇。舉凡悲憤復仇的《趙氏孤兒》、《竇娥冤》,淒美情愛的《西廂記》、《牡丹亭》,帝王后妃的《長生殿》、國破家亡的《桃花扇》,或直到當代都不斷被影視改編的《雷峰塔》等,不但愛看、更擅長再創,讓這些故事流傳百年。
 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汪詩珮帶我們跨越時空,爬梳中國戲劇有何魅力?能流傳百年,跨越時空與觀眾的心靈溝通。
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汪詩珮帶我們跨越時空,爬梳中國戲劇有何魅力?能流傳百年,跨越時空與觀眾的心靈溝通。
攝影/陳怡瑄
戲劇──動盪時代的烏托邦
中國戲劇成熟於13世紀的元雜劇。元雜劇具備宮調、曲牌,格式嚴謹,作者也有一定的文學造詣。然而當西方戲劇在公元前5百多年的古希臘時期已鼎盛,為何中國戲劇卻到13世紀才真正開始呢?
汪詩珮指出:「綜觀中國戲劇史的興衰,重要的轉變常發生在非漢人統治的『征服王朝』時期,如元朝誕生元雜劇,清朝興起花部亂彈、表演藝術趨於成熟等。王朝的替換對一般讀書人而言是天崩地解,科舉制度也隨之中止或變化,然而,也因此打破階層、體制等既定束縛。當文人考取仕途之道遭逢巨變,只能另尋出路,戲劇正好提供文人遁入之天地。同樣地,讀者與觀眾對戲劇作為娛樂、寄託之需求,也帶動劇場及伶人演員的興盛。」政治、社會、人心的轉變,造成文學的量變與質變,中國戲劇可說是因應時代動盪而生發出的文體。
元代雜劇的題材相當自由,什麼題材都能寫。汪詩珮說:「元雜劇就像古人的單元劇,篇幅短,情節涵蓋才子佳人愛情、家庭倫理悲喜、犯罪偵探判案等等,也涉及歷史政治、孤臣孽子等以古喻今者。」
「還有一個特色。」汪詩珮接續說:「元代雜劇有一類以『悲淒』、『憾恨』為調性,其收束屬於『不完滿』的結局。」
如《漢宮秋》和《梧桐雨》以帝王后妃的生離死別及追思作結;《西蜀夢》抒寫關羽、張飛魂魄的黯然神傷,以及劉備夢境的孤獨淒涼;《介子推》刻畫人臣遭棄的心酸與哀怨;《東窗事犯》以岳飛的一縷幽魂訴冤作結;《趙氏孤兒》以趙孤醒悟身世的悔恨交加與誓言雪恨告終。這一類的戲,以死亡、魂訴、悼憶、遺恨為敘事核心,是元雜劇中獨特的品類、殊異的美學。
 元代雜劇中有一類以『悲』為調性收束。圖為《感天動地竇娥冤》其中一折情節版畫,右為女主角竇娥。
元代雜劇中有一類以『悲』為調性收束。圖為《感天動地竇娥冤》其中一折情節版畫,右為女主角竇娥。
(約17至18世紀初。圖片來源/wiki)
如果說,元雜劇中的此類,反映『以悲為尚』的審美態度,則明代以後南戲、傳奇的「團圓」套式,則著重表現以旌獎、喜慶、合歡為尚的心理取向。
「因此,元雜劇流傳到明代,其結局常遭改動。」汪詩珮舉例,《趙氏孤兒》是最典型的例子;原來「一本四折」的戲被加上「第五折」,讓趙孤在第五折中復仇雪恨,並以結局之獎善罰惡替代冤屈與憾恨之意。又如元雜劇《竇娥冤》第四折,竇娥父親雖於劇末替女兒平反,但竇娥冤死結局無法改變,因此明人改編《竇娥冤》為傳奇《金鎖記》時,便令鬼神營救竇娥,使之闔家團圓,歡喜結尾。
大團圓及其例外
直到明亡入清之後,終於出現一部打破大團圓收尾之戲,就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孫孔尚任(1648-1718)撰寫的《桃花扇》。
《桃花扇》以南明王朝之崩塌為念,箇中原因之複雜,難以忠奸二分法簡化處理。故事表面上看似描寫侯方域與李香君的愛情,實則劇中人物眾多,包括帝王將相、忠臣佞賊、書生士子;也包括各式小人物,如說唱伎者、青樓妓女、書商畫士,作者以深心「側寫」大時代中的小故事,於戲曲中暗蘊春秋筆法。汪詩珮指出,孔尚任實際上是效法孔子,以戲曲寫一部「南明春秋」。
男女主角侯方域、李香君許定終身後很快就被拆分,將近兩年一直無法相聚,直到南明弘光皇帝敗亡,兩人分別逃到棲霞山中,終於在七月十五日張道士為崇禎皇帝亡魂追薦的法會上相遇,此時已是正戲的最後一齣。
「按照明傳奇慣例,兩人相見之後就是團圓結局。可是作者安排張道士下得壇來,到兩人面前怒斥,將他們的定情之物桃花扇撕裂擲地,罵道:『你看國在那裡,家在那裡,君在那裡,父在那裡,偏是這點花月情根,割他不斷麼?』男女主角當下竟頓悟分別,各自隱居入道,成為戲劇史上難得一見的『離散破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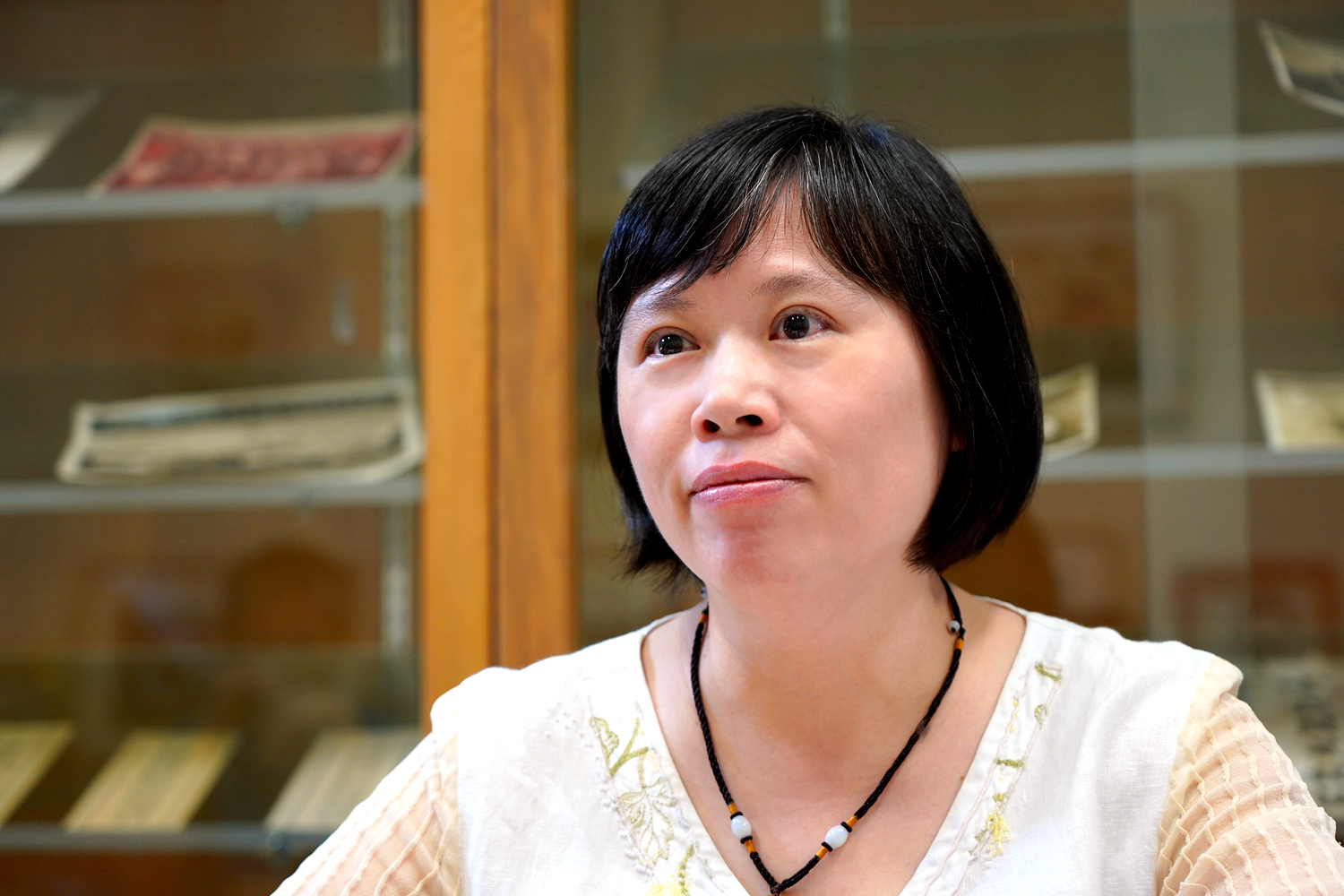 「我們想理解戲劇的變化,要回到歷史文學文化的脈絡去找,我們才能夠解釋,為何戲劇呈現這樣的樣貌。」汪詩珮說。
「我們想理解戲劇的變化,要回到歷史文學文化的脈絡去找,我們才能夠解釋,為何戲劇呈現這樣的樣貌。」汪詩珮說。
攝影/陳怡瑄
汪詩珮笑言,年輕時無法領會此一破局的用意,直到自己深入研究後才明白,夫婦旌獎團圓的明傳奇襲套,其內在意義是藉由夫婦人倫指涉倫常體系、道德秩序的恢復與完整。然而,明朝已亡,五倫之首的君臣關係已破,當此天崩地裂、倫常毀壞之際,豈有愛情置喙的餘地?因此,戲劇中的夫婦人倫也無法善終。
「明代戲劇固守的團圓結局,孔尚任在明朝滅亡後決然打破,這也是《桃花扇》特殊的編劇手眼。」汪詩珮提到,除《桃花扇》脫去團圓結局的窠臼,另一部清代傳奇《雷峰塔》──即眾人熟知的白蛇傳故事──更有著特殊的變化。
《雷峰塔》角色形象的翻轉
汪詩珮先問:「大家對白蛇故事的人物印象,大多是白蛇、青蛇為有情之妖,許宣(後來轉變為許仙)為負心之人,法海佛法過於嚴厲,對吧?」旋即又說:「但是這些人物形象,在早期的《雷峰塔》故事中並非如此。」
清中葉改編的《雷峰塔》傳奇源自晚明馮夢龍(1574-1646)的白話小說〈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早期的文人改編者為黃圖珌(1699-1752後),情節多沿襲小說文本,突出於「白蛇的妖氛」、「許宣的受害」、「法海的拯救」,並未針對新時代提出新觀點,也忽視觀眾反應,導致演出後迴響不佳。
事實上,清中葉商業劇場流行,觀眾不滿足於原作敘事的道德教化性,故梨園裡的伶人考量觀賞者的喜好,開始改編白蛇戲曲,為人物添加個性與情感,開發出新的情節敘事與表演方式。
「那麼,伶人面對觀眾的反應也呼之欲出。」汪詩珮說明:「觀眾對白蛇的同情、對許宣的質疑、對法海強力干涉的不滿,塑造出『妖亦有情,佛卻無情』的劇本與表演。另一位文人改編者方成培(1713-1808?)則參考梨園本,將「情」的因素置入,使文人本從譴責蛇妖的立場,開始接納情之力量。」
 雷峰塔於北宋太平興國2年(977)完工,民國13年(1924)9月25日年久失修的雷峰塔磚砌塔身坍塌。圖為坍塌前的雷峰塔近景,1917至1919年間由美國社會學家甘博(Gamble,1890-1968)拍攝。
雷峰塔於北宋太平興國2年(977)完工,民國13年(1924)9月25日年久失修的雷峰塔磚砌塔身坍塌。圖為坍塌前的雷峰塔近景,1917至1919年間由美國社會學家甘博(Gamble,1890-1968)拍攝。
圖片來源/wiki
研究發現,《雷峰塔》於乾隆朝的眾多改編現象,與文人、伶人、商人、觀眾喜好交織,甚至與乾隆皇帝、皇太后都有關係。
「不過,從清中葉的文人本、伶人本到今天的改編本,人物形象的轉變與差異,是否還有『關鍵文本』提供轉化的痕跡?」汪詩珮從思考問題到完成研究,花費了20年,最終於日本天理圖書館發現一部《後雷峰塔傳奇》,以「白蛇後傳」為主題,彌補了《雷峰塔》演變過程一個「失落的環節」。
《後雷峰塔傳奇》大約成於乾隆晚年至乾嘉之際,可視為《雷峰塔傳奇》的續集。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後傳」,翻轉原作人物既有的正邪設定,並開創出新的因果與情節。
「此劇以青蛇為主角,讓她也找到一位人間伴侶秦繼元,而這位秦氏書生一出場的志向就是嚮往與異類精怪結合。戲中還出現釋迦如來的師父燃燈古佛,藉古佛之口定調法海為拆散姻緣的罪首,還讓皈依的許宣因為負心而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劇情以拯救白蛇為主軸,每一位在《雷峰塔》中出現過的人物,在戲裡形象都歷經翻轉、逆轉、甚至重塑,令人大呼過癮!所以《後雷峰塔》又名《稱心緣》,故名思義,是一部能讓觀眾稱心快意之戲!」
汪詩珮認為《後雷峰塔傳奇》的重新出世,能為學界補齊《雷峰塔》的演變過程,並讓世人認識到,中國戲劇也能編出具抒情性之外,帶有強烈情節性與反抗精神的「續集」作品。作品的「改編」與「重詮」,既要承繼傳統、又需開創新局,才能引發當代觀眾之共鳴。
重詮再造
在我們的時代,「重詮再造」的作品仍然不少。汪詩珮以臺灣劇作家田啟元的《白水》(1993)為例,作品以白蛇故事為基礎演出全男版,該劇的法海象徵父權結構與國家暴力,而白蛇青蛇則挑戰既定的主流價值,隱喻當代的同志與多元成家議題。臺灣1/2Q劇團的《亂紅》(2012)改編《桃花扇》,突顯原作的精神意境,以劇場幻境及重組敘事將孔尚任的史筆隱喻表演出來。
 《亂紅》為1/2Q劇場第七號作品,首演於2012年5月,曾獲得第11屆台新藝術獎評審團特別獎。
《亂紅》為1/2Q劇場第七號作品,首演於2012年5月,曾獲得第11屆台新藝術獎評審團特別獎。
圖片來源/二分之一Q提供。陳又維攝。
「戲劇最迷人的地方,就在於潛藏的『隱喻』。」汪詩珮強調,包埋在古典戲劇的隱喻,能賦予後人詮釋作品的空間,為原作注入新生命。
「不過,重詮難在如何抓到原著意涵。」汪詩珮總結改編者的最大考驗,是如何維繫原作的精神。她分享梵谷寫給弟弟的信中一段話:「我在尋找先輩們創作時的記憶,從色彩的角度尋求對於同一個對象隱隱約約的共鳴。如果我表達的跟他們不一致,那就算是我自己的解讀好了。」
汪詩珮認為這段描繪,正指出重詮兼具「既往」(先輩)與「開來」(自己)的雙重性質。無論是中國或西方的古典戲劇,想在當代延續生命,融入新觀點、開啟新思維,才能讓百年前的戲劇反覆地重生,與無數觀眾的內心產生共鳴。
採訪撰文/班與唐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汪詩珮(2008)。遺恨與超脫:元刊雜劇中「以悲為尚」的幾部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汪詩珮(2013)。在「戲劇性」與「意境」之間:戲曲美學觀的初步貫串建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汪詩珮(2015)。清代「白蛇戲曲」傳衍中的「伏線」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本著作由人文·島嶼著作,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
本著作由人文·島嶼著作,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