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一提到中國史,我們就會想到「中華文化五千年」?「中國史」真的有五千年了嗎?
這些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歷史概念,其實是這一百多年來才逐漸形成的。如果穿越時空回到百餘年前,要找一本叫《中國史》的書恐怕都很困難,今天我們熟知的「中國史」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究竟是什麼因素形塑了我們對中國史的認知?要解答這個問題,或許可以仰賴史學史研究的幫忙。讓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劉龍心教授帶我們爬梳近代中國學科體制形成的歷程,重新認識我們自以為熟悉的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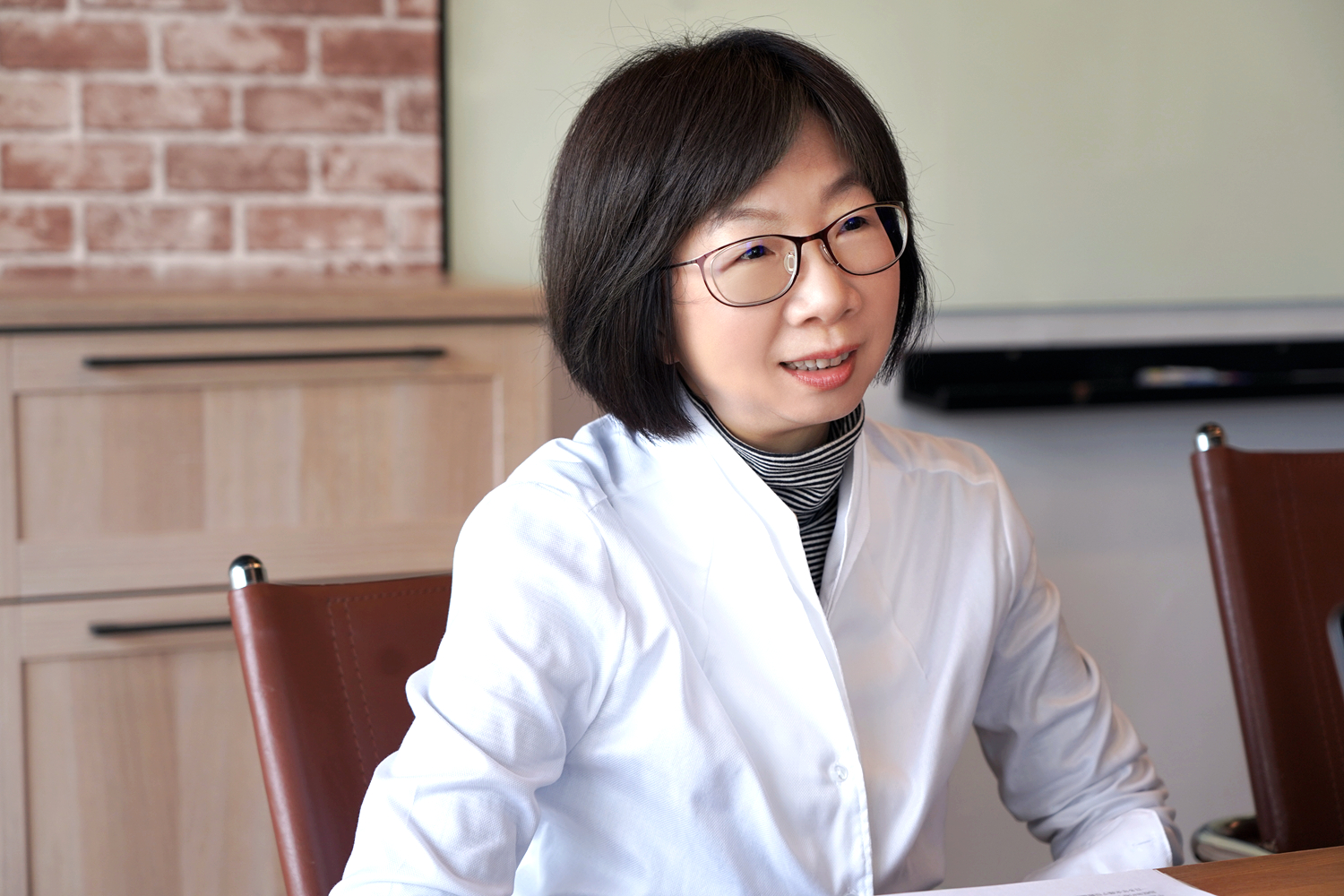 劉龍心從史學史爬梳近代中國學科體制轉型的歷程。
劉龍心從史學史爬梳近代中國學科體制轉型的歷程。
攝影/陳怡瑄
我們熟悉的歷史知識怎麼來的?
史學家往往都在寫別人的歷史,卻不見得關心自己歷史。劉龍心回顧自己最早從事近代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心路歷程時說:「一開始我只是好奇自己學習歷史這麼多年,卻不知道歷史系的學生為什麼要修通史、斷代史、專史、專題和史學方法一類的課程?而中國史課名有些叫上古史、中古史,有些卻以朝代命名,這中間到底有什麼區別?」在尋思這類問題的過程中,才慢慢發現養成自己的這個學術環境,其實不過是一百多年前才逐漸形成的。
僅僅一百多年,學科體制造就了我們今天的學術環境、教育制度和知識觀點,也改變了我們觀看「過去」的眼光。劉龍心表示:「我們太習慣從今天的學科視角來理解歷史!渾然不覺我們看待歷史的角度和古人有什麼不同。」透過史學史研究,她才了解「自我」是如何養成的,也對近代歷史知識形成的過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形構民族國家的歷史
談到「中國史」,可以往前追溯到清末民初,以「中國史」、「中國通史」、「國史」命名的著作才漸漸多了起來。用「中國」串聯過去一個一個朝代的歷史,把「中國史」看成是一個從古到今,連續不斷的歷史進程,其實是很晚近才出現的觀念。
在學科體制形成前後,有些史學家開始嘗試從民族國家的角度書寫歷史。劉龍心以梁啟超和傅斯年為例,說明這樣的變化。二十世紀初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直指傳統史學的「四弊」、「二病」所造成的惡果;批評傳統史學家只寫帝王將相的歷史,既不知朝廷和國家的區別,也不重視群體,幾乎沒有一部作品是為了國家、國民而作。為此,梁啟超大聲呼籲歷史應為當代活著的人而寫,「民史」才是歷史書寫的核心。這種帶有激越民族情感的觀點,在當時獲得很大的迴響,刺激後來一波波以民族國家為對象的寫史風潮。
 1903年前後的梁啟超。
1903年前後的梁啟超。
圖片來源/wiki
劉龍心表示:「我之所以注意到民族國家的歷史,是因為思考傳統史學和現代史學的差異而來。」她強調現代史學無論在觀念、方法、材料和書寫形式上,都和傳統史學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當我們去研究某個歷史問題之前,似乎更應該先去釐清導致此一根本性差異的原因為何?她說:「在我看來,導致中國傳統史學向現代轉化的關鍵因素,就是民族國家的出現。」
1920-30年代史學家開始嘗試用考古發掘的方式,探尋中國歷史的起源,即表現出民族國家對歷史的影響。這時傅斯年發表了〈夷夏東西說〉、〈周東封與殷遺民〉等文章,以「地域─民族」的觀點取代傳統夏─商─周的「朝代」系譜,打破「古史同出一源」的觀念。由他所主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早期的考古工作,基本上也都是在這樣的古史框架下進行的。特別是「城子崖」發掘,確立龍山文化之後,傅斯年和他的考古團隊幾乎非常確信濱海和鄰近地域,有一種出自周秦時代的固有文化,可以證明中國民族的東方起源。
傅斯年不惜動用大批人力物力,以地下考古的方式證明中國民族起源於東方,為的就是要對抗清末以來法國學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和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等人提出中國人種、文化來自西方的說法。傅斯年的觀點和史語所考古發掘的成果,在當時的考古學界引起很大的震動,並且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直到1970年代前後才被中國大陸考古學界以六大區系的「滿天星斗說」取代。從這個例子來看,傅斯年以夷夏東西對峙的格局,建構了那一代人對古代中國雛形的基本想像,而史語所的考古發掘路線,則證實了他對國族起源的根本理解。民族國家之於歷史研究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學術乃「國家」公器
民國以後史學走向專門,學院化、獨立化、專業化的條件逐漸成熟。因應現代民族國家而出現的歷史學,往往會透過一套科學、實證的研究方法和外在機制——如學術機構、社群組織、期刊論文、書評和審查制度,來鞏固它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在學科體制建立之初,構成學術社會的外在條件仍然保留不少人治色彩和彈性空間,特別在一個金錢、物資都極度缺乏的年代裡。
劉龍心談到中日戰爭期間,傅斯年為解決「居延漢簡」延宕多年始終未能整理出版的故事時說道:1930年由中國和瑞典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額濟納河流域的漢代烽燧遺址發現了一萬多枚漢代簡牘。後因抗戰爆發,團員四散,整理出版進度嚴重落後。傅斯年出面將這批漢簡送往上海商務印書館照相出版,1940年漢簡印出後,又由他主導,將漢簡暫時移往美國國會圖書館存放,1965年才由史語所具名領回臺灣。今天典藏在中研院史語所的「傅斯年檔案」裡,保有許多關於此事的來往信函。
傅斯年在這件事情上,不但出面多次寫信給西北科學考察團早期團員馬衡、袁復禮、袁同禮等人,說明即刻出版的必要性,情詞激切。同時積極運用私人關係,向中英庚款董事會的朱家驊和杭立武請求經費,協助降低商務印書館印刷、出版的成本,並且堅持版權必須歸屬「國家」所有,並強調:「此物乃國家之公器,任何人不得而私之。」
 座落在臺北的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紀念館與參觀者。
座落在臺北的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紀念館與參觀者。
圖片來源/wiki
傅斯年是一個有強烈國家觀念的人,他認為一切的學術資源、成果、聲譽,背後代表的都是國家。只有將材料「公開化」,才可以刺激國內學術研究蓬勃發展。也許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傅斯年處理「居延漢簡」的方式不無爭議,他甚至不避「學霸」之名,也要達到目的。不過劉龍心提醒我們:就像敦煌石窟裡的文物遭西方人搶劫一空的故事一樣,在那個年代裡,大部分的人沒有國家觀念,怎麼可能知道什麼是「國寶」?對傅斯年來說,手段可以是舊的,目的卻必須大公至正。「在與國際漢學界爭勝的大前提之下,公與私,新與舊,國家與個人,都可以有另一種安排和解釋。」
歷史是社會建構的產物
今天的學術環境和知識結構,已經和19、20世紀初有很大的不同,歷史學關注的課題也和以前很不一樣。
劉龍心表示:在梁啟超和傅斯年所處的年代裡,史學家努力嘗試把歷史當成建構國族的工具,而一百多年後的今天,絕大多數人卻可能根本渾然不覺民族國家對我們的制約和影響。歷史研究者在研究風潮轉向後,也極力避開相關課題,以為就此可以擺脫民族國家的歷史思維。但劉龍心認為:「歷史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只要民族國家做為現代知識和制度的基本框架不變,我們就不可能無視於它所帶來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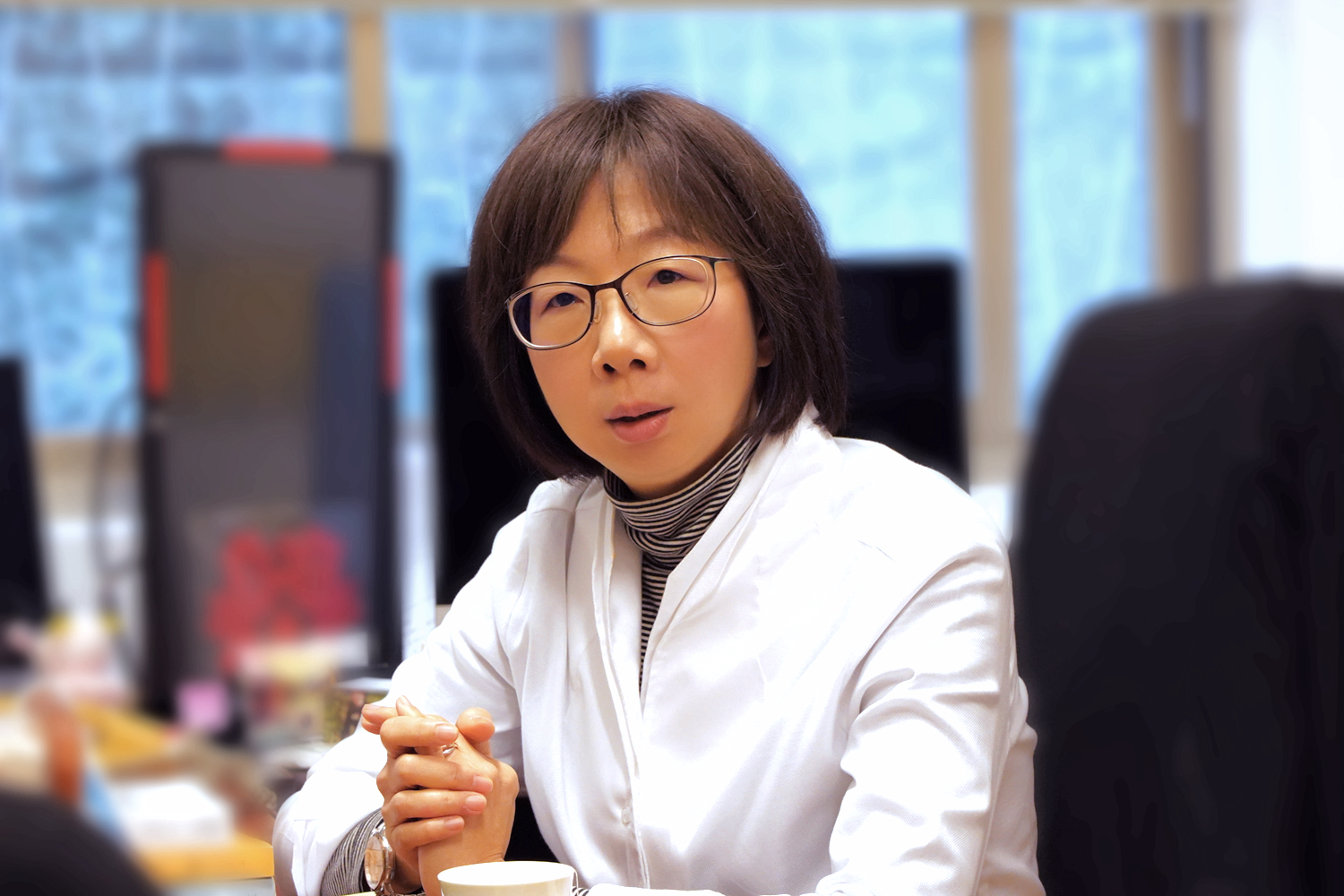 是什麼影響了我們對歷史看法?劉龍心從史學史的角度解構其中的成分。
是什麼影響了我們對歷史看法?劉龍心從史學史的角度解構其中的成分。
攝影/陳怡瑄
劉龍心回憶起自己的成長過程,見證臺灣從戒嚴到解嚴的轉變,使她即使研究的是過去,卻難以忽略當前社會的變化。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上,臺灣一樣要面對民族國家帶來的考驗。事實上,現代學科體制早早就把政治、社會、教育、文化和歷史牢牢綁在一起,牽一髮而動全身。
就像梁啟超發表〈新史學〉和清廷頒布新的教育章程,幾乎落在同一個時間點上一樣,歷史知識的變化必然伴隨政治、社會、教育的變遷而來。我們的下一代怎麼理解「過去」,絕大部分來自他從小所受的歷史教育,而歷史教育又和歷史研究終始存在著一種「互饋」的關係,因此當歷史教育成為政治和意識形態角力的戰場時,其實透露出民族國家仍然是歷史研究者無法迴避的課題。
探尋新史學史研究的可能
歷次的課綱調整,一般人最在乎的只是「比例」問題,關心臺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各占多少百分比。可是歷史教科書裡承載了多少民族國家的歷史思維和意識形態,卻很少人在意。
「其實我們的下一代相信什麼樣的歷史為真、什麼樣的歷史不可信,或是學院中的歷史研究者如何思考歷史問題、怎麼運用材料,從什麼角度、什麼眼光選擇、安排這些材料,都和我們所處的時代有密切的關係。」劉龍心強調,民族國家的歷史思維悄悄地改變了我們面對過去的方式,創造了一個帶有「目的論」色彩的歷史軌跡,讓我們以為歷史一定會朝著更進步、更現代、更美好的方向前行。
也許,在歷史研究愈來愈走向多元的今天,史學史已經不需要像一百年前一樣,以迴護民族國家的歷史書寫為目的,然而史學史仍然是當今我們反思歷史知識和當代史學的重要基礎。劉龍心表示:今天的歷史研究者是不是還秉持「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觀念?認為直接證據比間接證據有效?相信只要有足夠的史料就能如實的還原過去?或仍然把神話、傳說排除在歷史的門牆之外?堅持詩文、小說雖然可以「證史」,卻反對詩文、小說也是歷史的一部分。
這些看似「祖訓」的歷史方法、觀念仍然牢不可破的迴盪在今天的歷史學界,民族國家看起來被消解了,但是支撐它背後的那套「科學論述」和學科規訓,仍然左右著我們今天的歷史思維。
而史學史之所以重要,就在反思、提醒做為歷史研究者的我們,如何覺察這些我們曾經相信的觀念、方法和歷史論述,是在什麼情境、脈絡下產生,且讓我們信以為真的?持續探尋史學史未來的研究方向,關注近代歷史知識的轉型,將是劉龍心接下來努力的目標。
採訪撰文/班與唐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研究來源:
劉龍心(2019初版,2021修訂二版)。《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臺北:三民書局)。
劉龍心(2018)。〈從文化復興到文化重塑──戰後臺灣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史」書寫的轉折與蛻變〉,《思與言》,第56卷第1期,頁1-74。
劉龍心(2017)。〈地志書寫與家國想像──民初《大中華地理志》的地方與國家認同〉,《臺大歷史學報》,第59期,頁119-170。
Liu, Longhsin (2011). “Historical Lessons and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in the Late Qing Examination System”, Brian Moloughney and Peter Zarrow ed., Transforming History: The Making of a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p. 75-102.
劉龍心(2016)。政學、藝學與史學─近代中國歷史知識的轉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人文社會學者國內訪問研究)。
劉龍心(2008)。近代中國歷史知識的形成與傳播。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本著作由人文·島嶼著作,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
本著作由人文·島嶼著作,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