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系所林立與外文研究蓬勃發展,似乎是全臺灣的大學中自然的現象,然而這個看似外來的學術體制與人文資源,是如何進入臺灣的呢?
外文研究學科發展至今,在本土累積起卓然有成的研究成果,又是如何走到今天?有著什麼樣的故事?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王智明博士嘗試用一本書的篇幅回答這些問題,探索「外文研究史」發展歷程與意義?
「外文系」是怎麼來的?
「對外文系,我曾一直有一些困惑:爲什麼這麼讀?爲什麼這麼念?」王智明大學時期,對外文系裡的教學傳統與學派傳承懷有好奇。當時大多的前行研究僅以單篇篇幅,採斷代或文類為區分,試圖說明外文系的發展,這些文章各觸及一小部分,但始終缺乏一部能整體呈現學科史發展樣貌的專書。
因此,王智明心想,是否有可能,把外文研究在臺灣的歷史發展寫出來?「首先,第一個困難是時間軸要如何劃定?這是一個『歷史走多遠和多深』的問題。其次,要如何呈現歷史圖景?這必須去凸顯一些特定人物;這些人物必須具有時代文化特徵,另一方面,還要有足夠的著作份量可以形成建置史的檔案。」
由於早期外文系並沒有什麼保留系所檔案的慣例,直到1980年代後才有較多被留存下來的資料。於是他與助理只能在塵封的倉庫深處,找尋零碎的資料一一翻印,諸如早年外文系開設的部分課程大綱。「這些零星的課程概述主要反映個別課程的具體內容,必須整合在一起,才能看出學門發展的軌跡。」這使他體悟到,要探究這個問題並不容易。
促使王智明寫作這本專書產生強烈急迫感的原因之一,是當他想採訪顏元叔老師的時候,顏老師已不復在了。王智明說:「重要的人將會在歷史敘述還沒浮現之前漸漸消失,因此2017年我決定儘快把這個歷史化的問題意識落實下來,也才有《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這本專書的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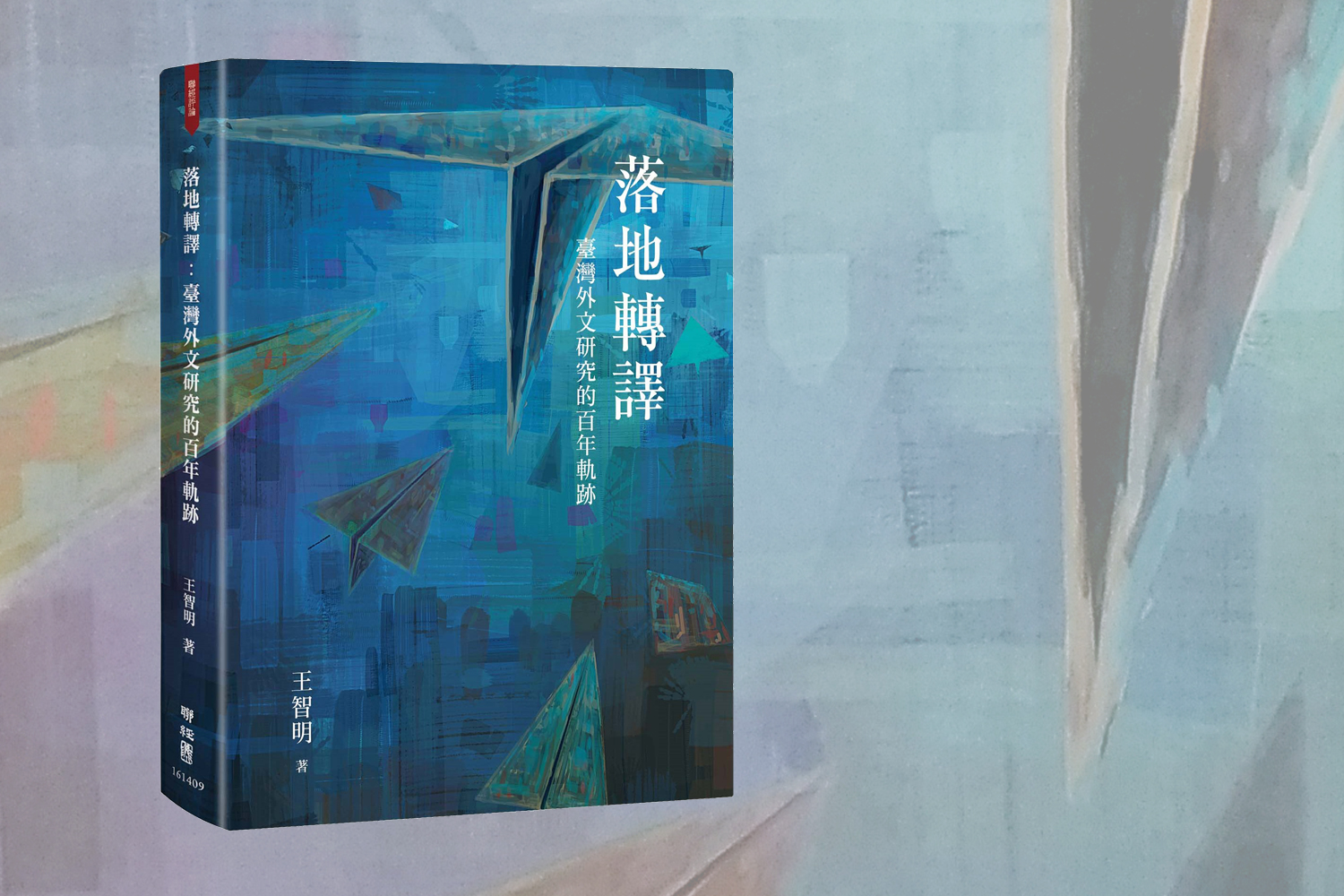 《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為科技部106年度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補助成果。
《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為科技部106年度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補助成果。
圖片來源/聯經出版社提供
文化邊界上的知識生產
王智明指出,我們不要把現今外文研究的發展當成必然是如此,或從來就是如此:「外文研究這門學科並不是單純的進口。好比我們讀英國的莎士比亞,重點在於我們怎麼讀莎士比亞?以及我們怎麼解釋爲什麼我們需要讀莎士比亞?在這兩個問題下面,所謂的『進口』,就具有『在地』的面向。」這個內外交界的地方,就是引發王智明論述的切口,也是他所強調的「文化邊界上的知識生產」。
這個邊界狀態很接近美國文化研究學者葛羅斯堡(Lawrence Grossberg, 1947-)對於「關鍵接合點」(critical conjuncture)的說法,葛羅斯堡認為這個接合點本身不穩定,是通過它與總體社會之間的交織和互動產生意義。
「我覺得外文系在整個歷史過程中,每一個片刻都很像是一個個接合的結果。」王智明肅然說道:「這個『進口』和『在地』的結合,我重新解釋爲『落地轉譯』。也就是在特定脈絡裡,每一個問題,每一個事件的發生,它其實都是特定歷史條件與意識的結合。」
「落地」突出了學術思想的跨地流轉,「轉譯」則包含了在地社群對外來思想的接受、理解和再詮釋。王智明強調,他想去追尋的是:外文系誕生、並成為一個學科體系的時候,是在哪些特定的歷史因緣中?他接續道:「因此,書的重心就放在突出與理解每個特定時空裡的結構條件,包含殖民現代性,冷戰、解嚴、全球化等,各種因素造成的相互影響。」
重返歷史時刻:在臺灣迎向西洋文學的學者們與相應的學術姿態
為了拼湊消失的外文學研究史,必須先透過重構歷史,觀看每個文化輸入的接合時刻。王智明緊抓了幾個特殊的時空節點:首先從晚清民初到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來看「外國文學」的移入與轉化;然後是在冷戰架構下以夏濟安、侯健和顏元叔為代表,看戰後臺灣(新)人文主義的流轉,如何透過學院體制和美援,形成既共構又分岔的在地實踐。最後梳理解嚴以來,臺灣外文學界進入「理論年代」之後,「文學理論」、「文化研究」和「族裔文學」幾個蓬勃發展的重點領域,如何從引介、轉譯到試圖融入在地關懷的研究發展,綜觀臺灣外文研究的發展走向,與邁向後冷戰論述的形構狀況。
王智明提及:「外文系──這個學術領域本身就是幾個不同力量的聚合。」學院必須面對西方,進入西方的文明體制中,把西方的文化傳統作爲自己學養的一部分,同時又積極努力保留中國文化的部分,這個特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一代的學者身上是相當明顯的。

對文學研究訓練出身的王智明來說,一頭鑽進高密度歷史化的檔案,搜集材料與建置資料庫,是一項十足的挑戰。
圖片來源/王智明提供
他以吳宓(1894-1978)為例。吳宓不僅教授西洋文學,同時編輯守舊派刊物《學衡》,也使用舊體詩翻譯英詩。王智明便解釋道:「吳宓這一代人認爲自己更大的作用是在中國文化上面,他並沒有要成爲一個西洋的文化人。」
類似現象也可以在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看到。蘇維熊(1908-1968)作為第一代臺灣本土的外文系教授,在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求學的背景,讓他本身的經歷具有殖民地與比較文學的視角,他對「自然文學」的主張和概念,來自日本轉介的西洋文學。
王智明透過詮釋蘇維熊「自然文學」論述形成的背景,說明外國文學的學術影響如何從倫敦到東京,再抵達臺北。進而影響臺北帝大英文科的師生,試圖以西方的眼光重新檢視自己的土地和文學。蘇維熊的「自然文學」顯現著一個殖民地外文研究者對「外地」(臺灣)主體的探索。從後見之明來看,「外地」的探索也成為了臺灣主體的召喚。
時序來到戰後,臺灣不再是日本帝國的「外地」,外文研究沿著冷戰的裂縫逐漸發展。
相對於前代學者透過他者眼光建立自我主體的狀況,十多年之後的文化人,在冷戰的政治氛圍與相應的資源裡,對於改造新文化的想像,已經進入到渴望融入西方文化的狀態。學者夏濟安(1916-1965)最具代表性,和前者形成對照。王智明一直想理解這些人:「他們到底在乎什麼?他們所處的歷史條件又是什麼?他們為什麼會從事這樣的研究?」釐清這些問題,正是這個研究的大挑戰。
當時的外文學者向美國取經,期以「新批評」和現代主義美學,改造外文教育和研究方向;同時,新批評的典範轉移中保留了民初外文學者主張的自由人文主義(liberal humanism)。他們以「比較文學」為自我定位,確保學術研究在威權的政治環境下保有相對獨立發展的空間,讓文學能反映人生,發揮改造社會的淑世功能。

時代相隔數百年、空間更隔著數千里,東方的學者究竟是如何識讀西方的文學呢?圖左為卞之琳(圖片來源/wiki)、右為歐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圖片來源/pixabay)。
其中,夏濟安從研究西洋文學,轉向研究中國的左翼文學運動。這一變化折射了冷戰反共的意識形態結構,如何影響臺灣學人在太平洋兩岸的知識社群中找尋自我定位,也反映了外文研究與中國研究或許因為冷戰,而有了更密切的共構和互動。
從《夏濟安日記》裡,王智明讀到夏及其友人,像卞之琳(1910-2000),原本都嘗試經營英文書寫,希望在英文創作的領域中闖出一片天地,但國共內戰與冷戰分斷的相繼到來,使得原來的設想有所改變。
「研究左翼文學運動並不是他原來想要發揮的領域,可是考慮留在美國和自己反共的心情,他就投入進去。夏濟安不是爲冷戰服務,但他也希望在文學研究的潛移默化中發揮反共的功效。」王智明指出在那樣的歷史情境,文學理想與民族命運,當然還是重要的時代命題:「這些人離開了中國,依然活在中國的歷史裡面。」
因此王智明認為我們不能將冷戰時期的種種文化表現,僅作為親美反共的現象而已,而是要去追問,在地的脈絡到底在這個「親美反共」的結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1950到1970年代的臺灣學者,不論立場,大抵都仍在中國的語境下思考,當時也沒有其他政治條件讓他們改變思考的方式。
「他們這一批人將反共信念內化在個別的文學信念裡,所以我們不能將政治與文學分開,也不能夠把歷史脈絡跟這幾位學者的書寫、學術實踐分開。」王智明強調這些學者在這兩層意義上,都存在某種程度上的矛盾,展現在個人身上。
叩問歷史變化對學術世界的影響
臺灣的外文研究大約在1960年代末逐漸成型,顏元叔(1933-2012)透過引介新批評,在人文主義的思想路徑上開展以民族意識為根柢的路線;不僅深化現代主義的批判意識,更形成一條文化上根植西方,卻在意識形態批判西方的進路,成為臺灣外文研究的開拓者。
王智明說:「到顏元叔、侯健(1926-1990)時,他用比較文學的方法重新探討中國文學,這是很大的貢獻。儘管他的研究可能不再是今天臺灣外文系所關懷的課題,卻呈現當時來自五四後的一代學者,他們試圖以西方研究方法,重新發掘中國傳統小說,尋找重建中國通俗文學的傳統。」
對當時的學者而言,外文研究不是冷戰脈絡下的區域研究,而是長期的民族人文工程。王智明提到,檢視夏濟安、侯健和顏元叔等戰後外文前輩的學術實踐,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凸顯外文研究的本土脈絡,如何受到冷戰意識制約,而本土學人如何在肅殺的政治氛圍中發起挑戰。王智明指出,「冷戰人文主義」背後涉及到自由人文主義跨越時空和兩岸政治之間的辯證,都是此輩學人留給外文研究的遺產和承擔。
而這份遺產隨著臺灣本土意識與後結構主義論述的崛起,使外文研究必須重新界定「人」與「文學」的意義,面對新的挑戰。1980年代,「文學理論」、「文化研究」和「族裔文學」三個領域興起,在共構、交錯間,為當前外文研究開出多重絢麗花火。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前身為創立於1928年的「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攝影/林俊孝
《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可說是敲開外文學門在臺灣身世之謎的試金石。從1970年代以來,在國外做西洋研究的學者,最後都做回中國研究,現在則可能替換成臺灣、東亞或華語語系研究,王智明認為現今國內與國際局勢的時移勢轉,大抵也包含著外文學科歷史變化的軌跡。
最後,王智明補充道:「外文研究的發展,除了不同省籍學者的參與,還有很多外國學人的貢獻。」例如1980年代,談德義(Pierre Demers, 1921-2002)等外籍傳教士在臺灣的外文系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文學造詣很高,啟發了許多的學生,但由於他們主要的任務是傳教,所以並沒有太多外文相關的學術論文或檔案資料留下,但是他們都在臺灣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儘管這段史事在書中沒有太多呈現,但這大體反映了撰寫這樣一本書必然遭遇到的挑戰,王智明坦言:「材料太多、了解太少,如何從故紙堆去理解歷史的變化對學術世界的影響,還需要很多嘗試,而這本書只是我勉力邁出了一小步。」
採訪撰文/李筱涵
編輯/張傑凱
王智明(2017)。落地轉譯:外文研究在臺灣的發展軌跡。專題研究計畫(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本著作由人文·島嶼著作,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
本著作由人文·島嶼著作,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