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這樣的場景:城市裡,半開放的後院變成菜園,左鄰右舍經過時也能自然地停下腳步,噓寒問暖。飲食與作物成了最好的破冰話題。都市人人或許沒有太多關於土地的記憶,但能透過交談學習彼此的生活經驗。耕作除了為求溫飽的生理層面,還擴及到社會倫理等精神面向。
這與我們腦海裡對「城市」及「農業耕作」的印象可能不太一樣。然而這樣的畫面,就出現在諾維拉‧卡本特(Novella Carpenter)的生活中。
回到城市
卡本特是嬉皮的孩子。小時候曾隨著家人在美國愛達荷州農場過著自給自足的農業生活,過去的經驗讓她在搬到奧克蘭後,嘗試於住宅後院廢棄或空地耕作,飼養雞、豬等家畜以作為晚餐的食物。作為嬉皮之子,她將目光放到城市社區裡因貧困所導致營養不良或糧食不足等食物主權問題:後院的收成不只留給自己,也分享給無家可歸的人,希望以此對抗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所帶來的各式糧食與社會不公等問題。父母輩沒有完成的反資本主義經濟理想,卡本特意圖在城市中實踐。而所有的行動與反思,都被她寫進《農場之城》(Farm City,暫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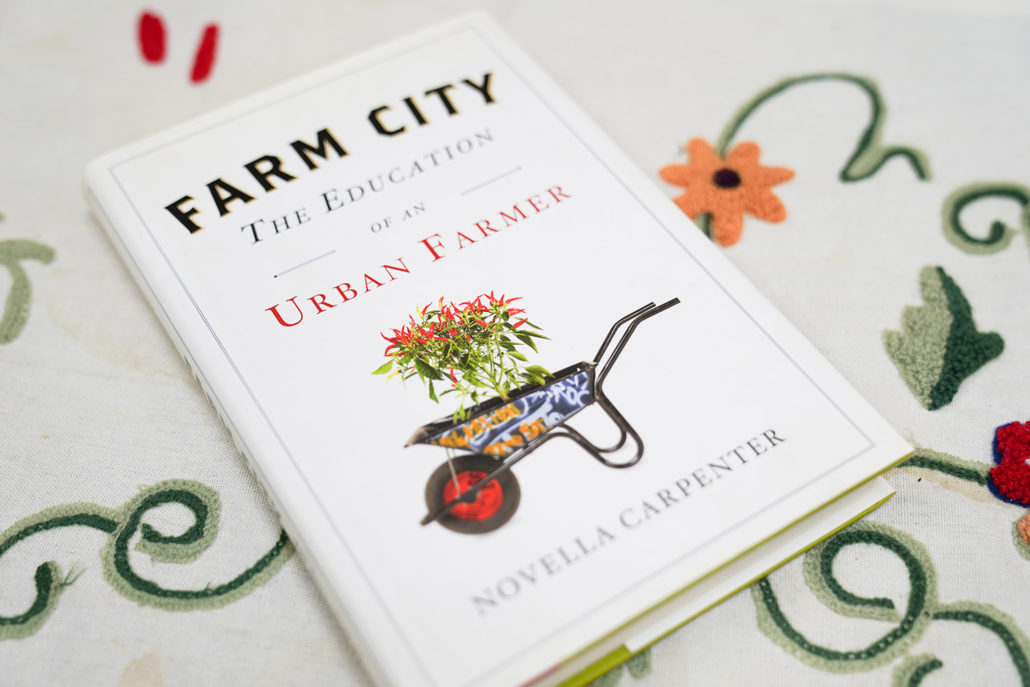
《Farm City》,Novella Carpenter。
攝影/陳怡君
身為城市農民,卡本特在奧克蘭的耕作屬於「城市有機農業」的一種。長期研究美國有機農業的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周序樺提到,有機農業作為一種反工業農業(Industrial farming)的耕作方式,大約發跡於二十世紀初期。當時因化學農藥與肥料對土地的汙染,英美科學家們對於土壤貧脊所帶來的體格虛弱等健康問題感到憂心,因此開始提倡各式「無毒」的耕作型態。到了六、七〇年代,嬉皮透過回歸田野與自然抵制資本主義經濟,認為身體與精神的健康同樣重要。二十一世紀前後,有機農業以嶄新之姿在城市再現,除了延續一貫的反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也企圖回應能源危機與氣候變遷等問題,嘗試城市耕作的可能。
事實上,在城市耕作並非近年首見。古希臘羅馬及中國,皆有曾於城市種植的紀錄。二十世紀上半葉,因一戰二戰時糧食缺乏,美國政府也曾鼓勵民眾在自家空間栽種及飼養家畜,除了供給自身需求外,也提供前線作戰使用。在台灣,也能於家戶的屋頂或陽台等空間看見蔬果的身影。而有機農業在「城市」發揮的作用,並非只以地域作為劃分,更重要的是其如何回應大規模農業工業所產生的政經、環境等倫理問題。
重新想像世界
當年嬉皮放棄在鄉村長居久住的部分原因,與「孤立」有關。前嬉皮士愛蓮娜.阿格紐(Eleanor Agnew)在她的回憶錄《從土地上回來》(Back from the land,暫譯)中提到,刻意離群索居的生活造成與人群隔離、現代與醫療設施的缺乏、失去文化活動等,過度理想化的結果終致失敗。
卡本特從上一代學習這樣的經驗,在城市中落實農業時,積極的將「耕作」轉變成一種與社會及環境「連結」的方式。原本因都市空間形成居民較為冷漠的態度,也隨著地景改變開始產生變化。
與其他類型的城市農業相比,卡本特更加崇尚傳統農業裡,勞動所帶來的安定感及獨立尊嚴。她對於農業的看法,引發我們思考「人與食物」的關係。同時,當農業從鄉村移往城市,「鄉村-城市」的邊界變得模糊,我們對於城市的理解也開始鬆動。周序樺說,在歐美國家,城市中的地景多半種植的是草坪或者景觀植物。但城市農業的出現,挑戰了他們對城市的想像:果樹就一定不美嗎?畸零地不能拿來種植嗎?城市是否就是不毛之地而不能有生產力?

美國城市一隅,人們利用空地種菜。
照片提供/周序樺

2017 年,舊金山藝術家 Mona Caron 在高雄苓雅區街頭彩繪作品「Outgrowing」。雜草與草藥的重生象徵著城市的生命力。
照片提供/周序樺
若街道旁的空地真的拿來耕種,也許會有人質疑:「怎麼能在公有地上種植私有財?」但如果上頭所耕作的作物開放大眾及有需要的人使用呢?這不是活化廢棄空間的好機會嗎?不只做為糧食問題與氣候環境惡化可能的解答,城市農業更引發一連串,關於人如何思考與認知都市空間、如何定義財產等問題,啟發我們重新思考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
如果這是最壞的時代,那就行動吧
氣候變遷的問題,已迫在眉睫:今年夏天,全球各地引發的雨林大火,其強度與密度超越平常居民「火耕」所應發生的景況;八月時,印尼總統佐威特宣布將遷都婆羅洲東加里曼丹省,原因便是現在的首都雅加達可能因海平面上升「沉入海底」;我們年年遭逢的颱風,風雨強度也在失控狂飆。
在專業分工與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國內的需求依賴進口,導致在糧食運送的過程中,產生許多溫室氣體,造成更嚴重的環境汙染與全球暖化。同時,過去的農耕方法所造成農業逕流的問題,也使得泥沙、化學肥料隨著水汙染土地。
迪克森.戴波米耶(Dr. Dickson Despommier)於 2010 年所出版的《垂直農場》(THE VERTICAL FARM),則是另一種城市農業的型態。戴波米耶認為,復育環境且仍擁有足夠及健康的食物選擇,兩者並不相違背,而「垂直農場」能滿足這兩個需求。
他提出藉由高科技與高資本,模仿與複製生態系統,利用水耕與氣霧耕技術在城市中建造「垂直農場」。農作物能在地生產,以解決因運輸糧食造成碳排放過多的困境。加上垂直農場理想上將建造成使農作物安全生長的環境,不只能減少水汙染,還能運用植物本身的蒸散作用處理灰水,讓受汙染的水還原成乾淨水源。
(Credit:World Economic Forum)
當然,在該書出版數年後的今天,已經有不少國家開始興建垂直農場。目前的確有技術層面的困難待解決,也並非書上提到的所有優點都實現。但作為理想模型,戴波米耶試圖提出的是一個可能的未來。只要克服技術問題,垂直農場便能自成循環,「自己製造的垃圾自己回收」便不再是夢。
無論你喜不喜歡,我們都不能自外於大自然。所有不同生態學分支的科學家,分別都得到相同的結論: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透過彼此相互依賴的生命更新循環,而產生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這是科學的建立基礎。──《垂直農場》,P.131。
面對當今的地球,多數人抱持負面消極的態度,認為環境將不斷惡化下去,甚至以「世界末日」來形容可預見的未來。然而對周序樺來說,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不論是卡本特或戴波米耶,他們都認為人類仍有積極介入的可能。也許真有那麼一天,人類與自然不再處於對立面,不再是彼此需要解決的問題根源。而我們對城市與農業的想像也將持續變化下去。
採訪撰文/陳怡君
編輯/陳怡君
周序樺(2017),美國有機農業與1970年代反文化運動,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本著作由人文·島嶼著作,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
本著作由人文·島嶼著作,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