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朗讀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吳治勳,近年與臺大醫院疼痛科醫師合作,探討病患那些難以言喻的「痛」。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吳治勳,近年與臺大醫院疼痛科醫師合作,探討病患那些難以言喻的「痛」。
攝影/林俊孝
如果你今天牙痛或背痛,應該會趕快去診所掛號,或者先吞個幾顆止痛藥,而不是去找心理師。但在美國的大醫院裡,疼痛管理中心(pain management center)約有半數人員由臨床心理師組成。疼痛怎麼會跟心理學扯上關係?「病好了」等於「不痛了」嗎?儘管每個人從小到大都嚐過各式各樣疼痛的滋味,我們真的了解「何謂疼痛」嗎?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吳治勳從高齡族群健康心理研究起家,近十年與臺大醫院疼痛科醫師合作,開始以疼痛為研究主軸。他在臨床現場發現,對慢性疼痛病患來說,「消除疼痛」往往才是就醫的真正重點:「我們常聽病人說一句話:『如果這個痛沒治好,我就完蛋了;只要我的痛好了,我什麼都好了。』這反映疼痛是一件多麼困擾人的事情。」
然而,有些痛是在手術、療程結束之後,仍然隱隱作痛,或許在生理指標看不出端倪,醫學影像上找不到痕跡,卻對病患造成真實的困擾,而此情況在生物醫學上,除了開止痛藥進行症狀控制外也。吳治勳指出,正因為疼痛的本質終究是一種主觀的心理經驗,除了疼痛者自己的表達,並無其他更直接的客觀測量方式,這種捉摸不定、缺乏實體的抽象性與主觀性,使得疼痛成為醫療照護上的難題。
「痛」是超越物理的存在
痛是什麼?大量心理學研究證據已顯示,疼痛無法被化約成單純的物理或生理現象。客觀上強度完全相同的致痛物理刺激(如電流),所引起的疼痛程度卻會因人而異。痛或不痛,甚至可能受到跨感官的調節:在接受相同物理刺激的情況下,當研究參與者同時看到大片綠色、或柔軟可愛的小貓小狗照片時,主觀上會比較「痛」;但若是看到紅色、針孔或血腥圖片,則讓人感覺更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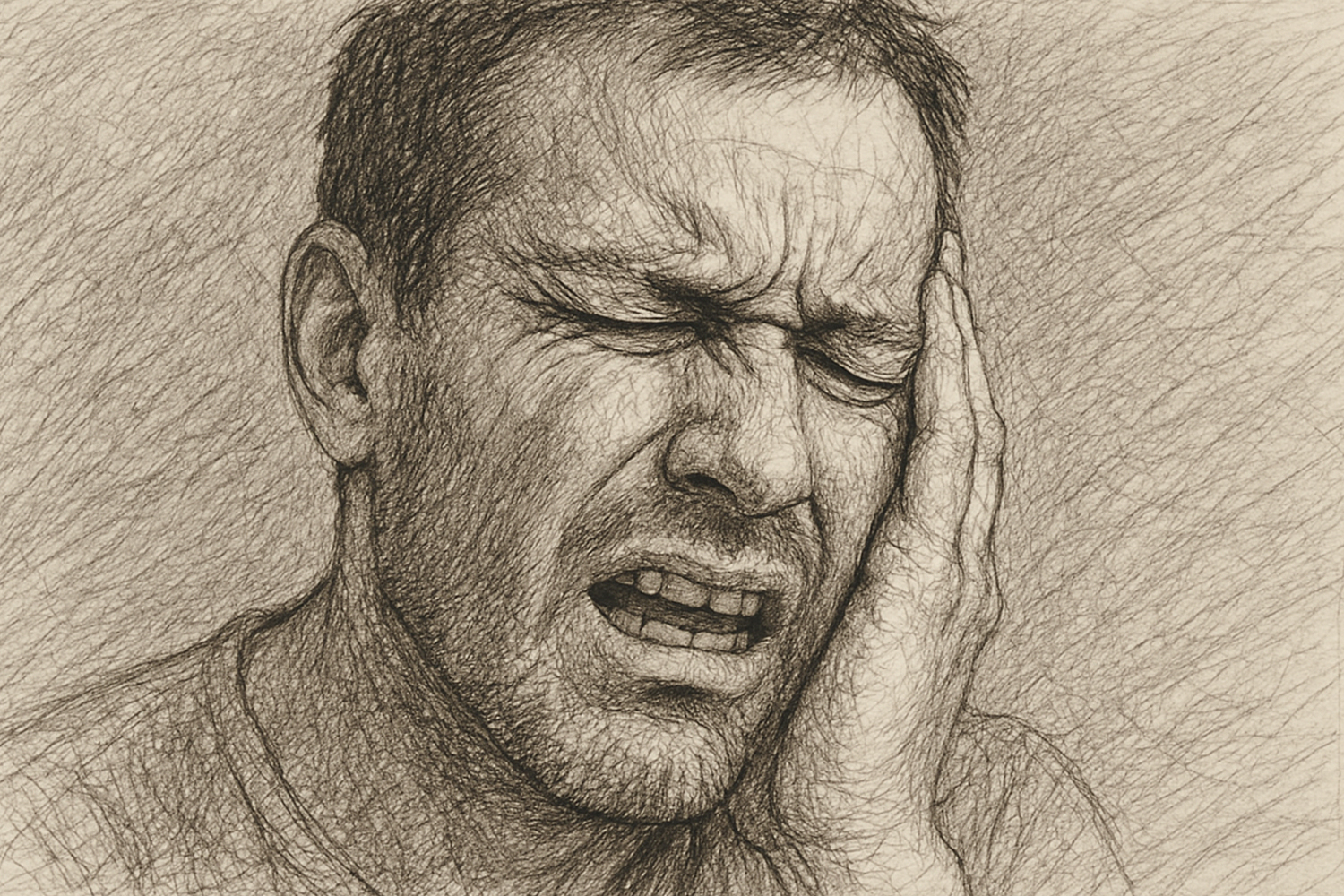 是近來心理學研究證實,疼痛無法被化約成單純物理或生理現象。
是近來心理學研究證實,疼痛無法被化約成單純物理或生理現象。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A close-up of a person’s face in pain, depicted in a sketch style.
痛,不只是身體的傷,而是複雜的心理經驗,涉及一個人的生命史、對不同刺激的敏感度和耐受度、當下情境脈絡,乃至於社會對於特定身分與疼痛經驗的集體認知建構。國際疼痛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ain)就在2020年修改了疼痛的定義,強調疼痛並非感覺神經元活動等客觀指標所能界定,而是同時受到生理、心理、社會因素影響的個人主觀經驗。
「早期醫界有個常見詞彙:『心因性疼痛(Psychogenic Pain)』,暗示病患報告的疼痛缺乏生理依據,『只是』出於心理因素。」吳治勳說,「這個詞現在已經不被使用,而是將基本觀念改變為:疼痛本身就是一種必須被尊重與關懷的心理經驗。」醫療體系看待疼痛的觀點已經轉變,從否認疼痛到聆聽疼痛,疼痛不僅僅關乎病灶的治療,更需要專業的臨床心理照護。
測量疼痛:「臺灣疼痛評估量表」的編製
說到這裡,疼痛的測量問題仍未解決。病患到底有多痛?痛了多久?這份疼痛對於日常生活與身心狀態造成了哪些影響?他們又如何理解自己的疼痛?在規劃任何介入方案前,都需要先進行全面且細緻的疼痛評估,但一直以來,臺灣卻缺乏一套具信效度等心理計量特性,同時符合本土社會脈絡的標準化測量工具。
吳治勳因此與臺大醫院疼痛科門診合作,聚焦50歲以上、有慢性疼痛問題的病患,展開一系列量表發展所需的資料蒐集與研究工作。從質性訪談、設計初版問卷、超過200位病患參與的預試、量化題項分析與調整,最終完成「臺灣疼痛評估量表」的編製。除了基本的疼痛程度與持續時間等問題,吳治勳還發現臺灣慢性疼痛病患的疼痛經驗,包含四大主題:疼痛造成的「衝擊」、面對疼痛的「無助」、試圖「逃避」疼痛,以及特別引人注意的──因疼痛而感到「丟臉」。
 你到底有多痛?痛了多久?臺灣正缺乏一套具信效度,同時符合本土社會脈絡的標準化測量工具。
你到底有多痛?痛了多久?臺灣正缺乏一套具信效度,同時符合本土社會脈絡的標準化測量工具。
圖表繪製/李季衡
意外發現:疼痛經驗也有文化差異?
「如果疼痛只是一種身體知覺,應該就會是跨文化皆然的相似經驗,但我們在研究訪談中發現,病患的疼痛經驗深受文化影響。」吳治勳解釋,回顧世界各國曾經發展的疼痛量表,從來沒有一個主題或向度和「面子」有關,臺灣很多病患卻十分介意這點。
從腳痛不願意拄枴杖,到偷偷吃止痛藥、不想被親友看到,「疼痛被看見」對許多人來說,似乎是件「丟臉」的事。吳治勳指出,害怕疼痛會讓自己丟臉的傾向,並沒有性別差異:「我們本來以為在男子氣概文化下,男性會比較怕丟臉,結果發現女性在意的程度不下男性。」
進一步分析,吳治勳還發現這種現象在高齡族群身上特別明顯。「老人家表面上常說不喜歡、不需要吃止痛藥,但健保資料庫顯示每年都有大量開給高齡者的止痛藥處方。更令人擔憂的是,如果為了不讓疼痛被發現,在日常生活中忍痛、不使用輔具、不去復健、依賴止痛藥,反而可能讓慢性疼痛持續更久,為身心都帶來更深遠的危害。」
社會性疼痛:不被理解的痛,最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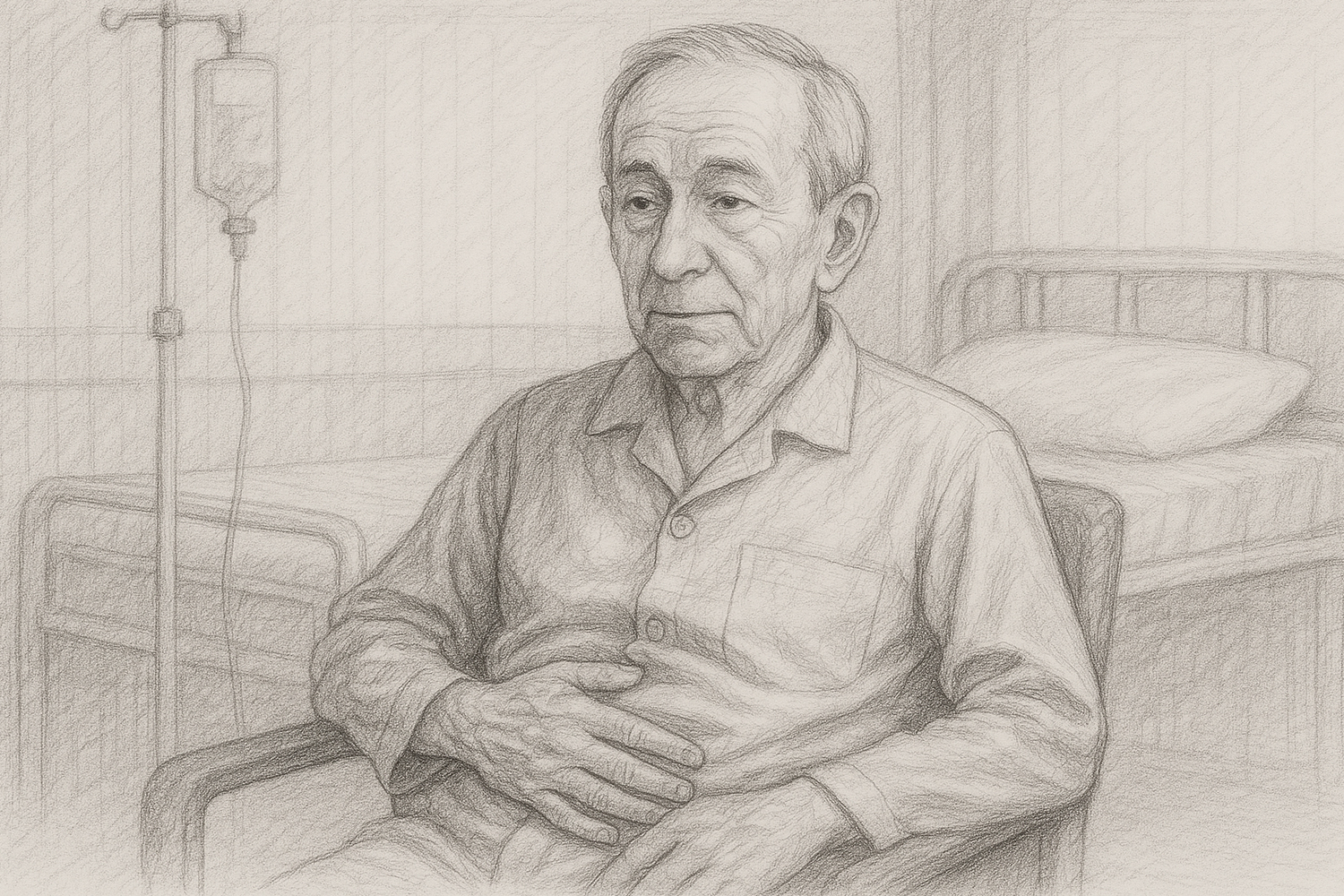 你是否也為了怕丟臉,又或者因為人與人間的互動,裝作一點都不痛的樣子。
你是否也為了怕丟臉,又或者因為人與人間的互動,裝作一點都不痛的樣子。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Depict an elderly person in a hospital, holding their stomach in pain, but with a facial expression pretending that nothing is wrong. Please use a sketch style.
除了文化因素,吳治勳更觀察到,疼痛經驗與人的「社會性」緊密交織。你的疼痛究竟是什麼樣的經驗,永遠只有你自己能知道,也因此疼痛常使人陷入孤立無援的社會處境。「我的痛沒有人理解」──對慢性疼痛病患來說,這種「社會性疼痛」伴隨的痛苦有時不亞於疼痛本身。
吳治勳分析,社會性疼痛的經驗主要來自兩個系統。首先是醫療體系,「我們最怕聽到醫生說『這刀開得很漂亮、很乾淨』,這句話聽在仍有疼痛不適的病患耳中,很容易被解讀成風涼話,代表『醫生不覺得我該痛』,衍生成自己被醫生丟包、無視的受傷感覺。」
另一個系統,則是家庭與重要他人的網絡。舉例來說,常有年輕病患被家人責難:「你怎麼過了這麼久還沒恢復?是不是不想工作,所以才裝痛?」吳治勳解釋,這正反映社會對於「典型的疼痛者」有著一套固定想像,與「年輕人=身體健康」的刻板印象相衝突,再加上集體文化信念中「年輕人就該去工作」的規範性工作倫理,造成比較年輕的疼痛病患反而容易受到親人的不信任、不理解。
吳治勳指出,當疼痛不被理解,為病患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僅止於心理層面,還可能透過社會壓力、寂寞感等生心理機制,讓短期的急性疼痛逐漸演變成長期的慢性疼痛:「就像一場考試,與上考場當天相比,長達一至數年的備考期間,每天一點一滴累積的壓力與身心影響更是沉重──從健康心理學的壓力模式來看,慢性壓力對人的殺傷力常遠遠大於短期事件。」
疼痛與孤寂:臺灣臨床追蹤研究
不過,疼痛有時也帶來轉機。利用臺大醫院疼痛科門診病患三個月回診一次的機會,吳治勳進行了關於疼痛與「孤寂(loneliness)」的追蹤研究,統計結果發現,病患的疼痛程度可以有效預測三個月後的寂寞程度,而且方向竟是「寂寞感降低」。進一步分析,這個現象主要發生在高齡者身上,也就是說,主觀報告疼痛越嚴重的高齡病患,整體而言三個月後越容易感覺比較不寂寞。
 吳治勳提醒,理解疼痛務必先能體認人的複雜性,才能夠真正聆聽病患因疼痛而發出的聲音。
吳治勳提醒,理解疼痛務必先能體認人的複雜性,才能夠真正聆聽病患因疼痛而發出的聲音。
攝影/W. Xiang
為什麼會這樣?不是剛剛才提到,疼痛是難以被他人理解的經驗嗎?「我們推測,這可能是因為高齡病患的身體病痛,更可能啟動身邊的社會支持系統。因為多數人對老人家的刻板印象跟年輕人恰巧相反,老人家更容易被理所當然視為『生病者』,所以當他們抱怨身體病痛,家人跳出來幫忙反而是『應該的』,是子孫盡孝道的展現。」吳治勳笑著說,醫院就常看到老人家第一次看診,身邊有三代同堂的一群陪病者。
但若到了第二次、第三次回診呢?疼痛對於寂寞下降的效果有多長遠,或者只是短期現象?另一方面,較年輕病患的疼痛似乎更容易遭到忽視,該怎麼辦?這些問題都還需要未來進一步研究。可以確定的是,疼痛與人的「社會性」息息相關,無法拆開來理解。
疼痛,終究是發生在「人」身上的事情,所以必須先能體認人的複雜性,才能夠真正承接因疼痛而發出的聲音。疼痛,不見得會在正式療程結束之後便跟著結束,更無法只以物理刺激的強度或生理數值概括。疼痛代表著一個人的主觀不適,代表著一個人需要另一個人(或另一群人)的傾聽、支持與理解,因此照顧疼痛,也就意味著照顧一個人,這便是心理學看見疼痛、理解疼痛的方式。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本著作由人文·島嶼著作,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
本著作由人文·島嶼著作,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