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一書是劉紹華耗費了十多年光陰,跑遍中國,為重現這些即將逝去的故事。
《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一書是劉紹華耗費了十多年光陰,跑遍中國,為重現這些即將逝去的故事。
攝影/林俊孝
你還記得書本裡的麻風病(又稱痲瘋、漢生病,本文均以「麻風」稱之)嗎?麻風病過去在世界各個角落都留下許多慘痛的故事與教訓,患者如果沒有接受治療,可能會在神經系統、呼吸道、皮膚與眼部出現肉芽腫,可能失去痛覺感知的能力,甚至面臨截肢、視力衰退的命運。因此,雖然麻風病的感染性很低,但由於人們深怕麻風病的副作用,做出許多令人遺憾的事。
2019年6月底,日本熊本地方法院裁定麻風病病患家屬的被害情形同樣是國家責任,日本政府應賠償總額3億7,675萬日圓(總額約新台幣1億元),這是日本第一次對麻風病家屬的國賠案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官方展開歷史上首度窮國家之力的巨型麻風防疫工作。在專業人力短缺、經濟停滯、技術限制和麻風歧視等不利情況之下,於1980年底,30年間將麻風盛行率降到萬分之一以下,達成聯合國的防疫標準。
中國究竟是怎麼做到的?又能帶給世人什麼意義?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劉紹華為此耗費了十多年光陰,跑遍中國,從個人生命、麻風病防疫、國家政治這三層歷史面向,重建1949年後中國官方展開麻風病防疫的動機、做法與結果,尤其針對最早投入麻風防疫的醫師及其後繼者進行探訪、研究和分析,保留這些即將逝去、被遺忘的故事。
緩慢是研究歷史的必要心態
「緩慢是研究歷史的必要心態,尤其是研究近在呎尺、事件相關之人依然健在的歷史。」
麻風研究歷程很緩慢,劉紹華說:「緩慢是研究歷史的必要心態,尤其是研究近在呎尺、事件相關之人依然健在的歷史。」如果不放緩步伐,看到什麼資料或突然有個想法,急於發表,很容易錯誤百出。
資料蒐集得越多,各種活動看得越多,相關人士交談得越多,「我對於描繪『真相』的信心卻越受挑戰。」劉紹華坦言,在田野調查中,很多次看到的景象都讓她震撼不已!拜訪過的山區麻風村普遍都很貧困,直到現在還可以看到老弱的病人在地形崎嶇的土地上爬行,甚至截肢處還長出一顆花椰菜般的碩大潰瘍,氣味濃烈嗆鼻。如今的麻風村狀況已是如此惡劣,可想半世紀前,年輕剛投入醫療事業的麻風醫師曾經歷過的心理衝擊。

麻風村至今還可以看到老弱的病人在地形崎嶇的土地上爬行。
照片提供/劉紹華
研究麻風中國就是我的田野
劉紹華從2003年以來,努力蒐集各種形式的歷史證據,也致力於獲得超越白紙黑字的資料,積極尋找曾經參與麻風防疫的醫療衛生人員、拜訪麻風村落與防疫機構、蒐集檔案文獻,其中最為關鍵之處,就是尋找老麻風醫生。
劉紹華歷經過歡迎、猶豫、拒訪,訪問軌跡遍及中國諸多地區-成都、南京、北京、雲南、廣東、上海、浙江、陝西等地,另外還有一些匆匆探訪或未訪問成功的地方,她直言:「中國就是我的田野。」

劉紹華走遍大江南北探索被掩蓋的那些年,圖為中國西南的麻風村。
照片提供/劉紹華
「他們的敘述中展現個人與集體情緒,以及那個時代的社會問題,有助我們去理解無數難以言說的個人生命。」最後,劉紹華成功訪問34位男醫師、11位女醫師,年紀最長者有96歲,最年輕的超過了60歲,這幾位開創中國達成消滅麻風成果的早期醫師,透過口述呈現過去文獻沒辦法紀錄的那些年。
強制的人道主義
當時面臨麻風病在世界上各個角落盛行,人們因無知而感到懼怕,在世界各國都留下慘痛的歷史,直到現今社會,遇上重大傳染病,如SARS、麻疹等仍是如此。
中國方面在1958年,根據官方22省的不完全統計,約有45萬名麻風患者,而1950年代歐美社會因發展較成熟,開始倡導消除隔離政策對麻風的污名和歧視,但因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才剛成立,政策、社會都未穩定,又面臨這麼恐怖的疾病,社會上充滿著恐懼,那他們如何來處理這樣問題呢?
儘管當時的官方文獻強調,強制隔離政策只針對有傳染性的病人,並非所有患者,尊重患者的自願與否。但劉紹華根據實地走訪研究,認為地方上很可能出現便宜行事的強制做法,使得官方政策執行變了調,她說:「在我的田野訪問中,多數病人都表示,入村是沒得選擇的事,因為家鄉的村民都希望他們離開。」

1921年,天主教傳教士在大襟島上建立麻風病院,圖為劉紹華2009年踏上島上的紀實。
照片提供/劉紹華
不過麻風村內的患者症狀輕重有別,就算知道自己得病,心理上仍抗拒接受這樣的事實。尤其輕微患者見到傷殘顯著的病人,還會感到懼怕,甚至憂心自己的未來,怕遭到同樣下場。甚至出現過患者因為恐懼逃回家中,反而被家人打死的案例,這部分案例僅是冰山一角,劉紹華指出:「麻風聚落及隔離政策本來是為了消除疾病負擔和歧視,然而實際執行上,卻離初衷越來越遠。」

1950-60年代中國全國大力建設麻風聚落,強制隔離的病患及從事醫療的衛生人員形成另一類受到歧視的群體,圖為麻風病療養院的戲台。
照片提供/劉紹華
汙名下的情緒勞動-麻風醫生
1950-60年代中國全國大力建設麻風聚落,在大量收容患者之際,醫療人力突然短缺的問題漸漸浮上檯面,但大多醫科專業人員不願投入被汙名化的麻風病及其防疫工作,因應不斷增建的麻風村,陸續增加的醫師從何而來?
「麻風醫生都是一群被人家瞧不起的人,去照顧一群被人家瞧不起的人。」
根據劉紹華研究指出,當時醫療衛生人員來源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民國時期有過麻風防治經驗的機構人員、醫療衛生人員、醫學院教授等。第二種,因在中共批評私有制的氛圍下,原本自行開業的醫師也可能被徵召。第三種從醫學院畢業生或病患中挑選培訓。
劉紹華說:「早期麻風醫生由於愛國情操與階級政治,投入汙名化的疾病防疫。在隔離的麻風聚落裡,又因見到患者而產生相當的衝擊、同情。多重心理糾纏,構成了麻風醫生的集體情緒勞動。」而這種類型的勞動,「是不會被寫入防疫歷史的。」
1950年代被指派為麻風醫生的知識分子,大多有著「不光彩」的政治背景,就像是麻風病患為社會底層一樣,這些醫師也集體淪為醫療界的底層。從事麻風防治最艱難的地方,不是身體上的疲憊,而是精神上的挫敗與多方投來的歧視,麻風醫生的專業被汙名化,以及社會上的污名同時發生,使得這些資深的醫事人員成為心靈受傷的醫者。
劉紹華回憶說:「訪問資深麻風醫生以來,經常面臨這樣的情況,他們講起麻風防疫的過往,有時與笑聲穿插並行的是酸苦的記憶,甚至偶爾不經意落下淚來。」她補充,一位麻風醫生甚至曾自嘲說:「麻風醫生都是一群被人家瞧不起的人,去照顧一群被人家瞧不起的人。」
老麻風醫生:「你做這個研究辛苦了!」
「這本書本來不會出現的。」訪談時劉紹華先這麼說,她說她原本想寫的是英文書,並且研究課題也不是如今這些,然而「一位高齡90歲的麻風醫生突然辭世,改變了我的決定。」
2013年資深麻風醫生、在研究路上幫助劉紹華良多的葉幹運教授逝世,帶給她很大的衝擊,劉紹華驚覺她所訪問的麻生醫生年紀已大,而她企圖從歷史做到當前的漫長研究,卻不知何時才有結果?「我希望在還來得及之前,讓他們(資深醫生)指正我的可能錯誤,讀到我的書。」因此劉紹華決定重新斷代研究範圍、改變書寫語言,都是很艱難的挑戰。且為了重新整理近期人物、在世者的歷史,劉紹華又經歷四年困難的摸索過程。
「但讓我得以堅持下去的最大支持,是來自於麻風醫生的鼓勵與他們的自由主義精神。」劉紹華說她長年來訪問的知識份子型麻風醫生,除了對不同立場的知識觀點、政治經驗、成長環境與世代背景,都能抱持著尊重與包容外,多位醫生對研究者的容忍和協助、善意與體會,都是劉紹華得以繼續堅持下去的動力,她寫道:「至於諸多讓我銘記在心的麻風患者、救助者以及基督宗教的善心人士與患者,他們的善意與協助都為我的動力加柴添火。」
訪談間談到如何打動這些資深醫生願意開誠佈公,劉紹華笑說:「需要懷著被拒絕的勇氣。」她提到,深刻的人類學研究就是要跟報導人具備感情,長年不斷的回訪,不斷的跟他們聯繫,並強調在這本書之前,不會因為取得什麼材料,就胡亂發表,「我覺得理解必須很深刻,否則傷了人、也傷了歷史書寫,所以我下筆非常謹慎。」
「我只是想要嘗試說明,有各式各樣的原因讓他們看到我的努力和誠意,」劉紹華回憶說:「有一位醫生從來不給別人去他家,以前也不接受訪問,有一次我去,託人把我的訪談大綱以及我的想法寫了長信給他,委託人叫我有心理準備,可能永遠無法訪問到他。結果那位醫生不但接受了,還邀請我去他家,訪問完還請我吃飯,吃飯時還夾菜給我,並跟我說:『妳做這個研究,辛苦了,不容易。』對我來說當下真的感動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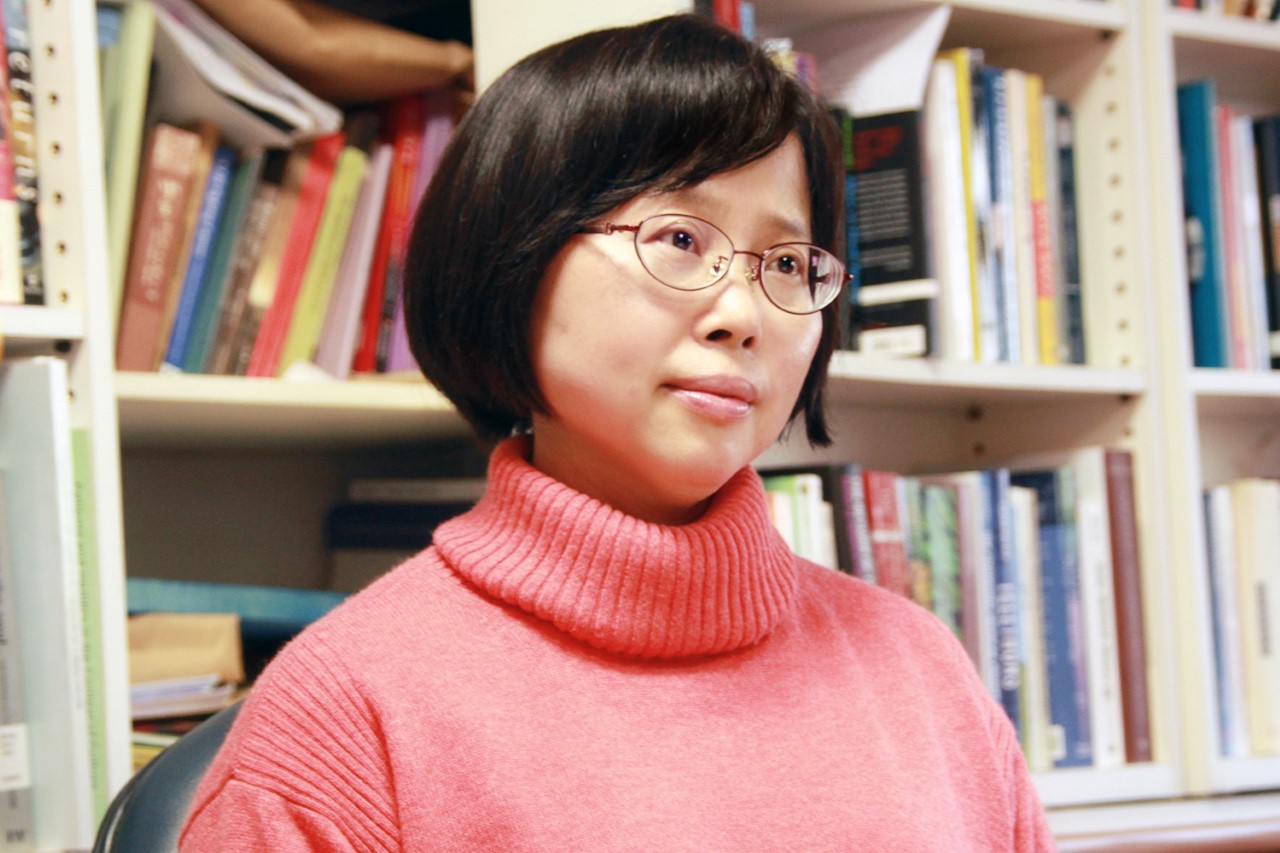
攝影/林俊孝
劉紹華從麻風患者身上學到生命的韌性,也從醫師與救助者身上學到可貴的人性。在漫長的研究與書寫過程中,她也發展出了一種堅持,劉紹華說:「我把自己當成一座橋梁,練習彎腰、承擔與跨越,因緣際會扮演起連結過去與現在、隱微與清晰、底層與公眾之間的研究書寫者角色。我有幸被人接納、聽其述說、見證歷史、體驗生活。既然幸運如我,無論有再多困難,我都得負重盡責地把這本書寫出來。」
採訪撰稿/張傑凱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研究來源
劉紹華(2016)。當代中國疾病治理的變遷:以麻風病為例。科技部 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劉紹華(2018)。《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臺北︰衛城出版。

 本著作由人文·島嶼著作,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
本著作由人文·島嶼著作,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